外语学人 | 王士惠:父亲和周公的友谊——忆周光耀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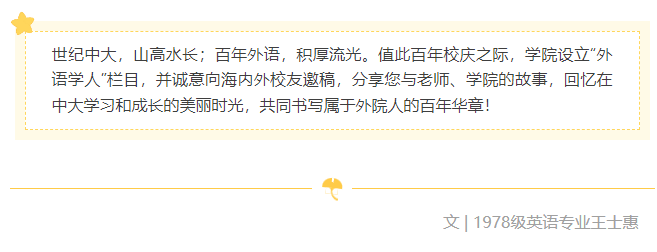
从20 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周光耀老师就在中大外语系任职英文副教授和教授,一直到退休。从50 年代初到60年代未,我父亲王多恩在外语系任教,和周先生共事接近20年。两人不但是合作愉快的同事,而且成为好朋友。

在我的记忆之中,周先生结婚较晚,一直住在校园北面的单身教师宿舍。每年除夕夜,父亲喜欢邀请这位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王老五”到我们位于中大西南区的家吃年夜饭,我也有幸认识了周先生。我那时候很小,不知道周先生为什么这么受父亲欢迎。父亲于50年代院系调整从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调到中大,周先生长时间在被合并到中大前的岭南大学外语系任教,在调到中大前,父亲和周先生素未谋面;另外,周先生比父亲差不多年长十岁,可以想象两人之间会有年龄“代沟”;还有,父亲初到广州,听不懂广东话,也不太了解岭南文化,周先生却是“生于斯,长于斯”,地道的“岭南人”。可是共事不久,父亲和周先生便成了好朋友,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只记得吃年夜饭时,周先生都笑眯眯地向大家点头问好。还记得他爱喝点美酒,每当举起酒杯,他的笑容会变得更加灿烂。后来时间久了,在家里,我们会习惯地把周先生称呼为“周公”。当然,见到周先生本人时,我们几兄弟还是毕恭毕敬地叫他“周伯伯”。
不记得是哪一年,从父母亲那里听说周公要结婚了。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叫结婚。只记得一个星期天,父母把我领到了中大小礼堂东面的一幢两层高的名为“教师之家”的红砖绿瓦楼房,去参加周公的婚礼。在那里我见到了周公,当然也认识了新娘子周伯母,我们后来就私底下称她为“周婆”了。只记得在婚礼上吃了一块奶油蛋糕,美味至极。回想起来,周公当时也有四十几岁了吧,记忆中的周婆也不是妙龄少女。听说周婆是位工人,经朋友做媒与周公认识结缘。我至今不知道周婆的名字,但就记得她朴实慈爱、和蔼可亲,待我们尤如亲生子女。
周公成家后就不再住校园内的单身宿舍,也没有申请校园内的住房,而是搬到广州中山四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的一座小楼房居住。父亲也就没有再邀请他来过年,但是每年都带上我们去他家拜年。周婆热情好客,做得一手好菜,我们倒成了他们的座上客。炸煎堆油角是周婆的拿手好戏,让我们吃了还大包小包地带回家过新年。
上世纪60年代初,不知是否由于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后;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几位外语系英语专业的老师 “雅兴”顿生,定期聚会,美名“春秋二季”。四位老师包括周公、王宗炎先生、吴继辉先生和我父亲。他们的聚会一年两次,到饭店用餐小酌,活动不带家属,仅限四“公”。“春秋二季”为他们几位老师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增进了同事间的了解,也建立起互相之间的友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不知道应该加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与周公商量后,决定组成名叫“为人民服务”的战斗小组,加上另外两位老师一共4位成员。他们是老一辈学人,毛笔字根底都不错,就当起了“文抄公”,每天回到系办公室抄写并张贴大字报,通过这种方式投身“文化大革命”。大约到了1968年,和大部分老师一样,父亲和周公被下放到广东坪石天堂山干校劳动。当时的周公大约60岁了,还要挑着行李铺盖,爬上粤北冰雪交加的高山,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依然是笑眯眯地面对一切。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时经常说,周公在山上,周婆在广州,因为她是工人阶级,不需要下放改造思想。周婆不时从广州给周公寄来一些点心糖果,周公总会拿出来和父亲分享。父亲感叹自己没有这个福气,因为我母亲在那一年去世了。
1970年,广东省高校改组,中大外语系专业外语被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从广州河南康乐园搬迁到广州东北郊的石牌五山,后来又转移到广州北郊的黄婆洞。我父亲从此调离了中大,而周公因为属于公共英语教研室,不需要被合并,就留在中大外语系任教。当时从广外到广州市区只有乘白云山班车,一两个小时才有一趟,班车在下午6点多钟就收车了。尽管交通极不方便,父亲每年春节期间,还是会挤公共汽车到广州市区给周公拜年,风雨无阻,年年如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大外语系专业外语复办,以戴镏龄先生为首的一批原中大外语系教师从广外调回中大,父亲就留在了广外继续任教。尽管不再是同事,父亲和周公还是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每年春节,必定给周公拜年。我们兄弟也必定跟随,因为周公和周婆家里一定会有美食招待。
1978年我入读中大外语系,不时在系里见到周公,得知他教研究生英文写作课。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笑眯眯的,从容不迫,波澜不惊,不知可否用“颇有老庄遗风”来形容。我1982年毕业,留在中大外语系工作。“子承父业”,我接替了父亲,和周伯伯做了两年“同事”。

--- sysufls ---
供稿:yl6809永利官网
排版、校对:庞紫莹
初审:庄坚彬
审核:黄源穗
审定发布:常晨光、于海燕
欢迎投稿&加入我们
sysuflser@162.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