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人 | 六个教师和一个用低调子说话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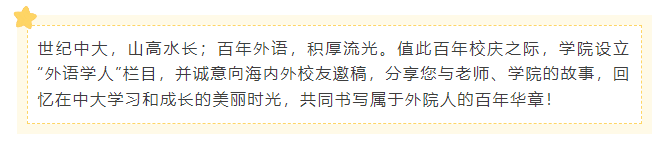
六个教师和一个用低调子说话的人
文|王宗炎
一
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后来会当英语教师。我的父亲希望我做官;我的曾祖父更希望我做官。我自己呢,大概想当大文豪而兼魔术师,因为我爱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太虚法师的讲演集和中国心灵学会的催眠术讲义。英语这东西,是中学课程中的一科,我得考个65至70分,但是再多就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了。
使我对英语发生兴趣的不是英国人,而是阿拉伯人——他们创造了文学名著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天方夜谭》)。对于一个十四岁的青年,这本故事集太引人入胜了。
在我们那个中学里,《天方夜谭》是三年级英语科的唯一教材。没有语法书,更没有语音书。在课堂上,老师从头讲到尾,就像广州广播电台讲《西游记》一样。这种做法,今天的英语教学法专家不免嗤之以鼻,可是对我们却有效。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所读故事离奇有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第二,教材中语言素朴,句法简洁。第三,我必须提到麦念勤先生,在英语方面他是我的真正启蒙者。
对于20年代中期的中学生,麦先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小白脸,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配上一副金丝眼镜,显得潇洒而高贵。他有点洋派头,可并不爱穿西服,见人也不爱说英语。
按今天的标准,麦先生恐怕不能算是很优秀的教师。他把每一个英语音节都念得清清楚楚,没有轻重之分。他讲语法显然讲得太少,不然我就用不着自己去苦读《纳氏文法》第三册。他从来没有讲同义词,所以我当时以为清真教的 genie 就是基督教的 devil,也就是佛教的“魔王”。
但是他有他的长处。他是个十分热心的讲课者。他人虽不高,嗓音可很响亮。他讲课时显然自己觉得饶有兴趣,所以越讲越精神,越讲越眉飞色舞。每个英语句子,他都译成流利的汉语,听起来毫不费劲。我本来想说他的教学法是“语法•翻译法”,可是细想起来,语法他也没讲多少,恐怕只能叫做“翻译法”吧?
“翻译法”——单纯的“翻译法”——在教学上能用吗?许多人会问。我不认为这是没有缺点的方法。可是也有人问过我:“不用翻译法,行吗?”有些补习英语的技术员、工程师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不能把课文译成明白流畅的汉语?为什么他老是在那里枝枝节节地讲单词,讲短语,讲什么主语,什么宾语,可从不直截痛快地告诉我们,一个长句子说的是什么?”
一朵花如果把它擘成七棱八瓣,就再也不是花了。麦先生的办法,也许还有可取之处吧?
二
1928年,我从家乡的廉州中学毕业,考进了广州yl6809永利官网预科。yl6809永利官网——我觉得这是个新奇的世界:课室里有电灯(家乡只有煤油灯),化学课有实验,图书馆阅览室里外国杂志很多,还铺上地毯。老师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有西服笔挺的青年留学生,而且除中国人外,还有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预科许多门功课都用原版英语教本,抱着一摞洋书走到课室去,我觉得挺神气。
只有一样事情不大称心——英语科胡美娟老师的教学法和麦念勤先生不相同,我很不习惯。
胡老师的模样倒挺叫人喜欢。短短的头发,金丝眼镜,闪亮的高跟黑皮鞋,宽袖子的苹果绿旗袍,是一个归国不久的华侨女郎样子。态度沉静而大方,说话时声音柔和,和麦老师的高亢调子成为一个强烈的对照。
我不习惯的头一项,是胡老师从不叫学生的名字,只叫第几号。她可能是把我们当足球队员看待,也可能有意避免记姓名的麻烦。不过,在我看来,我本是王宗炎,这会儿突然变为 No.16,未免滑稽。
我更不习惯的是,她从来不讲课。从走进课室起,她就不断地向学生发出连珠炮式的问题,No.8答不上她问No.9,No.9答不上她问 No.10。她那些问题,也不是事前叫人好好准备的,一般是先让你读一段课文,跟着就问这问那。事实上,有许多问题是要 No.16答复的。
我心里纳闷:问题都叫学生回答了,老师还干什么?
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略略明白胡老师的做法的妙处:跟她学了一年,我就能独立阅读几本书——Fifty Famous Stories Retold, Vital Problems of China,甚至 Washington Irving 的 The Sketch Book。我仍然不懂国际音际;我仍然背不出现在时态动词的定义;但是我具备了阅读浅易英语读物的能力。
胡老师的教学法,我不知道是她自己创造的还是从美国学来的,也不知道是否就是 Arthur R. Ellis 所谓 the problem-solving model,可是显然相当有效。不过,在她以后,我没有见过哪一位英语教师使用同样的方法。那可能是太旧——也可能是太新了。
三
在yl6809永利官网预科两年,我听过不少出色的老师的课。容肇祖先生使我对先秦文学和学术思想发生兴趣;陈仲伟先生(他只有一只耳朵)让我感到梁启超和历史研究的魔力;闻宥先生引导我读苏东坡、辛稼轩、纳兰性德的词。但是我怕做中文系、历史系那些训诂考证工作,于是进了英文系。
英文系教师换了好几批,各有特色。有善于讲课的,如史实烂熟的张葆恒;也有长于说明编剧艺术的,如教莎士比亚戏剧的Mrs. Kunkle。刘奇峰鼓吹唯美主义;黄学勤喜欢希腊悲剧;瘸腿的伍满意兴致勃勃地大讲我不大了解的美国新诗。但是只有一位教授对我影响较大,那是符佑之(W.J.B. Fletcher)先生。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描写符佑之。也许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吧。
他是英国人,可是青年时代跟一位中国姑娘结婚。
他懂得中文,并且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两本英译唐诗选。
他本是一个英国的副领事,可是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外交职务,到广州南武中学教书。
在我所见的外籍教师中,他是生活最清苦的。他从没穿过新衣服,脚上也永远是一双篮球鞋。
在文学方面,他有强烈的爱好,也有强烈的偏见。他喜欢Rudyard Kipling, Rider Haggard, Alexander Kinglake, Thomas Moore, CharlotteBrontë, Thomas Carlyle。他完全瞧不起 Thomas Hardy,认为Tess of The D'Urberuilles 只是一章章地模仿Pamela。他说 Alfred Tennyson 以后英国无诗人。
他的教学法最不值得赞美,因为那是最陈旧、最枯燥的。他把生词一个个写在黑板上,加上注解。他不讲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不讨论修辞手法。上他的课,你觉得他仿佛在教小学生。
但是他是最好的作文课老师。在一年级的时候,我虽没有选他的课,他也愿意给我改作业。由于他能写简洁清新的散文,他对学生自然有感染力。在改作文时,每一个词他都掂量过。他能告诉你表面相似的词在什么地方并不相同。上下文不动,他能一下子给你提出两三个可用的同义词。他指引你进一步读书,并且在你的作文本子上抄下他所心爱的许多诗句。别人觉得改文是苦事,他可觉得改文是乐事。
他有不少民俗学知识。他告诉我,西欧妇女戴帽子,原来是为了预防魔鬼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边。
他有许多不平凡的见解。有一回我问他是否基督教徒,他说不是。我再问,“为什么不是?”他的回答十分干脆和明确:“你读过《圣经》,就想去读宗教史。可是读过宗教史之后,你就再也不信上帝了。”
像一切抱有不平凡的见解的人一样,符佑之先生是苦恼的。他最后挑选了浪漫主义者的结局——投海自杀。在给yl6809永利官网英文系的遗书里,他这样写:
Life is short, but art is long.

《英译唐诗选续集》(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W. J. B. Fletcher
四
1938年,我到海关税务专门学校内勤班当学员。海关这地方,早先我是不愿去的。第一,海关是“国中之国”,洋人当权。第二,我的计算能力很差,可是在海关里你要天天跟算盘、帐本打交道。但是海关对于失业的大学生是有吸引力的。那里有金饭碗,报酬特别优厚;它还有铁饭碗,只要你规规矩矩,一辈子不愁被开除。
从家乡来到上海法租界麦琪路税务专门学校(上海市已经沦陷,租界是“孤岛”),我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教师。粗野诙谐的白俄 Anderson 教体育,拘谨稳重的意大利人 Antonio 教军操,说话结结巴巴的英国人 Fewkes 教验估学,年轻貌美的美国人 Emily Hahn教英文公牍写作(她爱抽大雪茄,上课时常常打盹)。中国教师倒一般不错:教务长梅其驹说英语口若悬河,李博士(记不得他的名字)讲经济学讲得很熟练,任锦祥谈缉私工作也具体而生动。
由于对历史有兴趣,我特别喜欢张似旭(Samuel Chang)的中西关系史课。他是东吴大学毕业生,英语流利,听说在国民党外交部当过什么司长。年纪不过四十来岁,中等身材,圆眼镜后面闪动着孩子气的眼睛,说话时气度安详,像是一刻都胸有成竹。
除当教师外,张先生还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同时又为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英文《大美晚报》)写文章。《大美晚报)由美国人 Randall Gould 主持,同情中国,反对日本侵略。正是因为这,我们佩服张先生,并且为他担心。
“张先生,你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吗?”有人在课堂上问。
“是啊,”张先生用低沉而缓慢的调子回答,“他们觉得我碍眼,寄过一包有毒的苹果给我”。
听到这话,全班学员都紧张起来。
“他们还派人把一只断手送给我,”张先生接着说。
“那么你不害怕吗?”
“我到别的地方住了几个月,避一避风头。后来我就回来了。”在讲这些事时,张先生照样气度安详,就好像谈论别人的事一般。
时间一天天过去,张先生每周按时上课,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了。但是几个月后一天晚上,我在《大美晚报》忽然看到一则黑边新闻。再注意看下去,那标题是:张似旭在德国餐馆被人刺杀。主笔 Randall Gould 为他写了悼词,但是不敢公开骂日伪特务,只说下毒手的是 superrats。
如果有人写中国报业史,他应该不忘记一个不太出名的人——张似旭。

张似旭曾任《大美晚报》记者
五
我是1946年回到yl6809永利官网外文系任教的,当时系内教师人数不多。到1948年,外文系忽然热闹起来,因为添了一批南来教授。不用说,这些人是因为禁不住从延安吹来的强风而避居广州的。后来他们各奔前程。有的回到北方,如俞大絪和吴宓;有的可再走远些,如李祁到了香港,梁实秋到了台湾。
在这一群“南飞雁”当中,我感兴趣的是梁实秋。第一,我读过《新月》派一些作品。第二,他是讲文艺理论的,我那时也正在担任文学概论课。我觉得,教这门课是一个苦差。我搞不通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也弄不懂梁实秋的人文主义。当然,对于蔡仪的新美学和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更外行。
我看过梁实秋的“论三一律”、“浪漫的与古典的”等等论文,觉得他有学问,可是学院气太重。我那时也是住在“象牙塔”里边的人,可是我住在最下层,梁先生却住在最上层。他和他的老师 Irving Babbitt所讲的那一套人文主义,我认为离开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太远了。但是他既然来到广州,机不可失,我总得去请教一番。
他住在文明路平山堂。想是由于新来乍到,房间里收拾得不太整齐。人胖胖的,穿一件半旧灰色袍子,谈起来活泼爽朗,可又带着淡淡的哀愁。
我自然首先提出人文主义。我以为他会进一步发挥他的高见。
“你要问国外的文学批评吗?”他摇摇头。“啊哟,对于这些东西,我早已 out of touch啦。这些年来,我只搞两个题目——杜甫和莎士比亚。”
文学理论不谈,我们改谈时事。前不久,我看过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叫做“罗隆基论”,说此人“识不如学,学不如才”。我料想他会在这个题目上再发表意见。
但是这他一点也不谈,倒是扯到当时的大学生助学金问题上去。他说,“这个问题这里闹得一塌糊涂,倒不如老八那里的办法好。”
他所谓“老八”,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出自他的口,我不禁一怔。
“老八的方法怎么样?”我问。
“他们干得公道合理。哪个学生得助学金,得多少,都公布,让大家讨论。不像我们这里暗地搞,争得面红耳赤,不能解决。”
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我心里想,从梁实秋的嘴里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评论,如果能报道出去,那倒是一个真正的scoop。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了。我不知道梁实秋现在怎么想,可是从我过去听到的几句话,我觉得对他的见识和性格应该客观地、全面地估量。

梁实秋
六
1954年夏天一个上午,yl6809永利官网三位校长都在办公室。头发灰白的许崇清校长开始看一本新杂志;精力饱满的陈序经副校长研究财务科的报告;胖胖的、惯用低调子说话的冯乃超副校长正在打开盒子,把眼镜拿出来。作为校长办公室的兼任秘书,我照例走到他们跟前,看有什么事情要办。
一个不速之客来了。那是钟一均副教授,政治课教研组的负责人。他皱起眉头报道一项新闻:“听说外语系正在争论苏联教材问题。有人说这种教材的英语不够地道,有人认为这样说是有意捣乱。对于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看?”
那正是全面学习苏联时期。马里采夫是政府的文教总顾问;凯洛夫的《教育学》是老师们的必读书;普希金以教育专家的资格在全国各地听课,滔滔不绝地发表评论。如果你对新理论不留神学习,你不是反动派也是个老顽固。
苏联教材有没有缺点呢?这个问题当时没听人提过。许校长显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不回答钟一均的话。陈副校长似乎吃了一惊,他轻轻地咳了一声,转过头来望着冯乃超。办公室里鸦雀无声,真是掉下一根针也听得见。
为什么外语系关于英语教材的争执要由政治课负责人来向学校领导反映呢?因为这虽是语言问题,可也是政治问题。
外语系使用苏联教材College English已经一年了。对于它,英语教研组主任骆传芳教授和多数教师一样,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经过跟爱人夏露德教授(美国人)一起细心阅读以后,他们的结论是,从语言角度看来,个别地方有不完善之处。
这个意见一透露出来,马上引起各式各样的反响。有人点头赞成;有人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可是占上风的是这样一些议论:
——骆传芳的英语能比苏联专家好吗?他满嘴湖北土音,连moon 都念成[moun]。
——骆传芳是由美国教会豢养长大的,老婆又是美国人。他准是美帝走狗。
——骆传芳夫妇自从由汉口调来以后,就跟广州那些亲美派抱成一团,这里难道没有鬼?
——党号召学习苏联,骆传芳可偏要挑苏联教材的眼。这哪里是讨论什么英语问题,分明是存心跟党唱对台戏嘛!
上面这些话,我也隐隐约约地听到过一些,现在在我的脑子里翻滚着,要求判断,要求解答。跟许崇清、陈序经、钟一均一样,我注视着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
冯乃超拿手绢把脸擦一擦,开始用低调子对我们说话了:“苏联教材嘛——”他停了一下,“我看嘛——”又停了一下,“也是可以讨论的。”
陈序经脸上露出微笑了。许校长点了点头。钟一均好像找到了丢失的门匙,他满意地转身走出校长办公室。
外语系的争论暂时平息下去了。骆传芳得救了。可是他在劫难逃,三年后,由于某些莫须有的罪名,他终于戴上了“右派”帽子(后来已经摘掉)。
60年代以后,学习苏联的口号不再高呼了,批评苏联教材当然再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但是理智战胜愚昧和偏见是不容易的,讨论苏联教材College English的英语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行为,人们——除了冯乃超——要经过整整十年才弄得清楚。

冯乃超
(原载李良佑等编《外语教育往事谈》,1988,上海)
---sysufls---
供稿:yl6809永利官网
转载编辑:欧阳璇
初审:庄坚彬
审核:黄源穗
审定发布:常晨光、于海燕
欢迎投稿&加入我们
sysuflser@126.com

